一名巴黎实习医生的抗疫日记:死亡嘲弄了医生的诊断
摘要: 参考消息网4月10日报道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蔓延,医护人员们艰难的抗疫之路受到关注。26岁的意大利裔住院实习......
|
http://blsw.qiuyi.cn/zlfy/ http://gxb.qm120.com/zllcyj/482.html http://blsw.qiuyi.cn/gxbzs/5101.html http://blsw.qiuyi.cn/zlb/zlbzl/753.html http://gxb.999120.net/tnb/fy/ http://blsw.qiuyi.cn/zgnmss/zgnmssfy/834.html http://blsw.qiuyi.cn/zlb/zlbyf/2166.html http://blsw.qiuyi.cn/byby/bybyby/928.html http://gxb.999120.net/wjz/fy/1346.html http://gxb.999120.net/gxbzs/107.html 参考消息网4月10日报道 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蔓延,医护人员们艰难的抗疫之路受到关注。26岁的意大利裔住院实习医生萝塞拉(化名)从3月23日开始,在巴黎一家负责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工作。本网已于3月30日登载她写下的6篇“抗疫日记”,记录了她在这场“战争”中的真实感受。现继续刊发她最新两篇“抗疫日记”,内容如下: 在这个隔离期的第18天里,我赤裸裸地醒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,从我睁开双眼时起,我就感到极度疲乏,不同于其他日子的疲乏,犹如一个警报在提示我,“放过你自己吧,今天将会很难”。 中午的时候开始下雨了,并且一直持续,越下越大。不过,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,至少和其他日子相比,没什么特别的。原本身体很好的L夫人在上卫生间时出现了不适;J夫人的家人在电话里大喊大叫;医疗小组缺乏团结并且在面对困难时解体。 医护人员现在如同病人和其家庭之间的桥梁。在这个桥上有一辆载着疾病和死亡重量的货车经过。有时,车辆过于沉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谴责打击,我极其重要的力量好像被一股旋风吸走了,我倒了下来。留给我的只有泪水,无声的泪水。 我工作的团队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家庭,只是它在我来之前就已经组建起来了,而且它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从容且仁慈地欢迎新成员。在这些阴暗的日子里,我没有真正地感受到被接纳、被保护和融入。我感到孤独。 自开始以来,我就知道这种考验将是沉重的、不可预测的、令人疲惫不堪的。我知道我不可能提前想象出命运留给我以及留给病人们的是什么。现在,我知道,我始终都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人知道。 这个周末我没有休息。我周六和周日上午都要值班。然后,购物、打扫房间、做饭、洗衣服,但是我感到精力充沛。 周六上午的班一直上到15时。很多工作,也受到很多触动:我一个人要照看11个病人,除非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去咨询主治医生。幸好没人催我,没人给我出难题,我按部就班地干活,周围是我的病人和一个优秀的护士、护工团队。 我来到办公室做准备工作。我开始整理所有有用的信息,每个病人有一页纸:夜班交接注意事项、早上的临床指标、可能要使用的抗菌素和其他药品,血常规,正在进行的输液,首次出现新冠症状的日期…… 然后,我去挨个看望病人,给他们做检查,和他们聊几句。没什么急事儿,我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抱怨。他们饱受病痛折磨,但是也有被隔离和孤立的痛苦。这种极度孤独影响了他们的精神状态。和他们聊聊是很有益处的。 像每天一样,我被自己见证的一些事深深触动了。然而,我不能深陷其中。我得保持冷静去面对他们。我突然就失去了一位很喜欢的病人。根本难以预料她会在今天离去,但是死亡却嘲弄了医生的诊断。我们在这边忙着阻止,但她执着地走上了另一条路。这位女士曾渡过了感染难关,重要指标也都不错,但是她的心脏在11时47分停止了跳动,她离开了这个世界,在安详中没有痛苦地离开了。还好,此时此刻她并不孤单。当时我刚刚离开房间,但护士萨比娜一直和她待在一起。 3月27日,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的罗歇·萨朗格罗医院,医护人员从一辆救护车上转移患者。(新华社) 参考消息网4月6日报道 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蔓延,医护人员们艰难的抗疫之路受到关注。26岁的意大利裔住院实习医生萝塞拉(化名)从3月23日开始,在巴黎一家负责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工作。本网已于3月30日登载她写下的5篇“抗疫日记”,记录了她在这场“战争”中的真实感受。现继续刊发她最新一篇“抗疫日记”,内容如下: 这些数字就是我所工作科室的概要。我亲爱的病人们就像苍蝇一样悄无声息地坠亡了。 在这场战争中,医护人员的使命是崇高的。医生不仅仅是大夫:他们要当护士、助理医师、社会扶助人员、心理师……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职业的全部含义,他们不再是“专职者”。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医生:每个人都在比平常做得更多、更好一些,去完成本不属于他们职责范畴的事情,大家都在互相帮助,没人惜力。 对待病人,我尝试着建立“三线”关系:医疗、身体和精神。首先我要掌握他们的临床病症,然后是他们的身体状况,最后是他们的精神状态。有时,当医生的就得脱掉大褂,坐在病人旁边,做一个陪伴者。 今天上午接近9点半时,我去看望G女士。我发现她在掉眼泪。这是一位基本上与世隔绝的女士,精神沮丧,当然也是一位新冠病人。她还能与人正常交流。她蜷缩在病床上,姿势像极了胎儿。嘴唇抖动,头有节奏地摇摆着,看起来很伤心。她的口水流到了衣服上,嘴边沾满了唾沫粘液。鼻涕也在往外流,氧气罩上都是鼻涕痂。 在进入病房前,我查看了她的体征指标,我很确定她呼吸稳定、血液循环正常。一进病房,我没有像以前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去查看吊瓶,而是先在精神上安抚她。我一边帮她调整躺的姿势一边跟她说话。我拿了一块毛巾沾湿后给她擦脸,随后在她的脸上涂了一些保湿乳。 G女士一直不停地哭,还断续地说:“谢谢,你真好,多谢。”慢慢地,医患关系确定了下来。我发现她的静脉滴注停了。我对她说:“女士,打吊瓶是给你的胳膊补充水分。应该换一只胳膊,要扎你的手部静脉而不是肘部。”仍在垂泪的G女士认可了。不幸的是,几乎没法扎针。很难找到她的静脉。 我得去找罗歇,这位60岁的老伙伴很有经验。他高大、帅气且很严肃。他来到病房时,G女士有点犹豫。她没有想到这样的天使会来到她跟前。罗歇一下子就扎到了静脉,然后就走了。我愣了一会儿,然后笑着对G女士说:“知道你有多幸运吗?给你扎针的是全院最火的护士。下次,我宁愿替你被扎!”G女士打从心底里笑了。这一刻,她含泪体味着幸福。 处于恐惧和信任煎熬中的G女士终于同意下床了。我轻轻地扶着她站了起来,她有点痉挛,僵硬得像块石头,移动困难。这时我提议:“要不我们俩来段华尔兹?来吧,把你的手放在我肩膀上。” G女士有点犹豫,然后顺从了。她靠近我,靠着我,然后紧紧地抱住了我。逐渐地,恐惧从她的眼中消失了,她的身体也变得很柔软。当我在她耳边哼起乐曲时,她完全由着我来带动她。 4月1日,在法国巴黎17区,工作人员为一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医护人员取样。新华社发 【延伸阅读】一位巴黎医护人员的抗疫日记:“是我杀了他!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!” 参考消息网4月2日报道 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蔓延,医护人员们艰难的抗疫之路受到关注。26岁的意大利裔住院实习医生萝塞拉(化名)从3月23日开始,在巴黎一家负责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工作。本网已于3月30日登载她写下的3篇“抗疫日记”,记录了她在这场“战争”中的真实感受。现继续刊发她最新写的两篇“抗疫日记”,内容如下: 周五,我上班迟到了一刻钟。我的科室主任朱尔当时正准备去查看病房。他并没有和我谈昨晚的死亡病例,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,我应该准时上班。这并不是他苛责,而是“战争中”的医院就是这样。 我打开电脑,发现G先生昨晚去世了。12小时前我和他的妹妹还交谈过。她后来再也没有打电话给我。我再也没听到她那忧伤的询问:“我哥哥,他会怎么样呢?” 中午,我已经完成了当天的巡查。我查询了两个今天新归我管的病人的资料,因为有一名住院实习医生同事感染了新冠病毒;我们两个诊室只有三个住院实习医生,病人要重新分配。 到了下午就忙乱套了。我尽可能快地来回跑,这都不够。患者们病情恶化了,我得在他们心脏停跳前介入,否则他们就可能失去生命。早晨病情还不错的T先生呼吸困难,他不断呕吐,需要静脉注射、抽血和上氧气。两名晚期患者开始出现疼痛,需要给他们注射药物来止疼。每次出入病房、穿过走廊以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,都要洗手、换衣服,但是没有足够的防护服,总之就是一片混乱。 在这种忙乱中,我还要写周末交接班医嘱,并且照顾两个新接手的病人:其中一个身体极度虚弱但意识清醒且很害怕;另一个是位年长的女性,伴有双极性症状并且很难回答医生的询问。要立即监控他们的血液循环和呼吸机能,以便在夜里尽可能早地采取必要措施。 我把在走廊里的女病人背进了病房。我检查其体征并完成了临床检查。她的情况显然不太好,但是病情还算稳定。我在检查记录上写下结果,并且尝试着在数据库中寻找其信息。我找到的信息不全,但是我联系上了她以前的主治医生。后者向我简述了她的病情:这位女士是从一家精神病医院出来的。我还有一个今天的情况报告没找到:它不是用电脑打的,而是写在纸上的。我准备去找一下补齐今天的材料,正好碰到了朱尔。 朱尔对我大发脾气,根本不让我解释,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。他只看到了资料有所欠缺,显然认为我是个粗心的人。“18时还拿不到一个病人的全面资料,这是无法接受的!”这种侮辱,在这种情景和心情下,我无法承受。那位女病人是17时45分到医院的,她的情况当时不太好。因此,在大致知道其情况后,首先需要确保她不受刺激、进行临床检查、查阅急诊医生的医嘱。我不可能同时把一切都做了。 缺失的情况报告最终在护士台找到了。朱尔给该病人以前的临床医生打了电话,最终拿到了全面资料。我开始写交接班医嘱,要求第二天抽血,整理一堆事情,并且和他一起处理一天中最后的工作。 一小时后,我还在哭,当然在病房的时候除外。朱尔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儿。我向他承认,因为没做到的事感到伤心,还有无助感、不安全感、让头儿失望的窘迫……朱尔还算绅士。他并没有真正地安抚我,只是不再生气了。他向我解释说,他的职责也包括在住院实习医生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督导他们。 接近晚上八点半,我离开了医院,感觉自己像一把脏兮兮、湿漉漉的拖布。我骑上自行车,一直哭。 日记五:“是我杀了他!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!”(法国《快报》周刊网站3月31日文章) 今天早上,我不想起床,困意很浓。但是闹铃一直在响,一遍,两遍,三遍。我深呼一口气,拥抱了一下维克托,然后起床。 我疲乏得快要站不住了。在浴室里,我坐在浴凳上开始淋浴,这是在投入医院脏乱且难以预料的一天之前最后的乐趣。 我还不知道周末诊室里发生了什么事,也不知道又有多少病人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只是知道,将会来到一个和周五不一样的科室。 一到医院,我就得知那位85岁的老爷爷在前一天离世了。我预料到了,为自己没能在现场感到遗憾。我想到了他的女儿,在10天时间里她不停地打电话,而她的父亲一直在与死神搏斗。 上午是视察病房时间。穿上防护服,脱掉防护服,洗手,安排氧气,把老年人扶上轮椅,听诊肺部,撤下吊瓶,读病历。 下午,我要为迎来一名新入院的病人做准备,但是病人刚送入急诊室就死了。另外一名病人已经替代了他的床位,不过要到晚上才能到。我明天才会见到他。 在我负责的病人中,有一名男子表现得很有攻击性。只要有一点不对劲他就情绪不安,他也有认知上的问题。他没法理解传染病正在传播而他已经感染了病毒,对别人来说他是很危险的。应该尝试着和他解释清楚。 “不,姑娘,别和我说这个。够了!你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背叛了我!我是一个自由的人,我一直都在缴纳社保,我有权回家!” 我向他详细解释,回家是不可能的,我是在执行当局的命令……真的没有别的办法。他很生气,大喊大叫:“出去!如果明天我还没回家,我就自杀!”这是住院实习医生经常碰到的场景,并非只是疫情期间。 P先生是一位89岁的病人,他可能很快就要离世。三天前,这一幕还难以想象。他身体一直不错,在家里和老伴独立生活。但是他的妻子感染了新冠病毒,她有些小感冒但已经康复。不幸的是,她把病毒传给了丈夫,后者的反应却完全不一样。老先生开始发烧并且脱水。几个小时后,他的病情开始恶化并被送到医院。 今天那位老伴给医院打电话,接电话的是科室负责人朱尔。老人的绝望让他受到很大触动,老太太认为他们55年的恋爱长跑可能就要终结了。她在电话里对朱尔说:“上次看见我丈夫,我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面。然而,是我杀了他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,但是如果不能和他道别就更受不了了。”于是,朱尔允许老人下午可以来探视一次。 一个半小时后,老太太出现在了医院。她的面庞紧绷。我们给她穿上防护服,并给她戴上口罩和防护帽,然后让她去病房。她很慢地走过走廊,实际上她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在跑。她是最后一次拥抱自己的丈夫,后者的生命正在一点点逝去。她拥抱还活着的丈夫,泪流满面。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…… 参考消息网3月30日报道 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爆发,医护人员们艰难的抗疫之路受到关注。26岁的意大利裔住院实习医生萝塞拉(化名)从3月23日开始,在巴黎一家负责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工作。她写下的这三篇“抗疫日记”,记录了她在这场“战争”中的真实感受。 我今年26岁,是巴黎一名全科住院实习医生。我被分配到一所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,直到疫情结束我都将在那里工作。 我男友是我要去的那家医院的一个部门负责人,他从3月16日起开始清空病床准备收治众多即将到来的新冠病人。我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什么。我是意大利人,20岁前一直生活在热那亚。2018年7月我拿到了毕业证,并来到巴黎开始当住院实习医生。 我在不到两年前才开始说法语,说话还带有意大利语腔调,用法语写东西还有点费劲。我喜欢读书,也喜欢写点东西,四年前我开始写书。在日记里,我将讲述未来几周里发生在医院和家里的事情。我知道: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之中。 总统马克龙16日所说的并不是耸人听闻,而是真正的事实。我们要准备经历一段特殊时期——“第三次世界大战”。作为人类我们应当骄傲,因为我们在不断进步。我们一直在相互争斗,但这次,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这还是历史上首次战争把我们大家团结在了一起,不分肤色、语言和宗教信仰。 这次战争可能会教会我们为何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,生命到底有多么不可预知……而直到上个月之前,我们还十分笃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高等、强大而不可战胜的物种。 在我们中间,有人原本计划要结婚、度假、生孩子、写小说、去旅行……现在,这些都不太可能了,一切都暂停、推迟了。只有死亡没有停下脚步,不过这不是安静地死去,也没有亲友在身边环绕。 这场战争迫使我们告别以往舒适安逸的生活。这可能很艰难、痛苦和沉重,也可能会显得很漫长。有时人们可能会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,可能会经历恐慌和无助,但是得学会适应。 日记二:“新冠病毒是白刃,它悄无声息地置人于死地,留下一片血海 ”(法国《快报》周刊网站3月24日文章) 前天,法国目睹其首位医生去世。我想维克托,他是我要去的科室的头儿,而且我现在更加胆战心惊。我明白自己不可能停止这样,尽管疫情好像在无休止地持续。 [8:00]我骑着自行车,任凭早上的风无情地吹在我脸颊上如刀割一般。这种痛苦是一个警告。为了赶往医院,我要用近半小时的时间,但挨冻要好过冒险在地铁里与某个人交叉而过。 [9:15]上午正在等待中过去。等待各个科室进行N次调整,等待医生和住院实习医生根据各种需要被重新调配;等待病人的周转,他们前来就医、被转走、死亡;等待各种行政命令……然而,在本能暗示我们跑掉的时候,应该接受这一切,保持不动。 [10:00]我在等着被调往某个科室的期间,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。我取回登陆软件的代码、工作服。我看了一些文章,咨询了集中病人各种问题的平台。 刚刚和我非常喜欢的同事萨拉打招呼,就有一名病人出现了呼吸困难。这个非常年轻的女子5天前刚刚生产。萨拉想要马上将她转去抢救,却没有床位了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她转往另外一家医院,可她的状况十分危急,促使医生们在考虑转走前是否有必要插管。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一做法,没有切开这个年轻母亲的喉部。人们将她抬上救护车,随后她朝着生或死的方向消失了。我们对此将永远无法知道。 [12:00]中午,我什么都没做,却觉得已经精疲力竭了。头儿叫我去办公室。危急时刻,他要我去专门隔离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的科室。我终于上战场了,浸没在痛苦之中,并将与死神作战,因为我知道,这场战争将不会有战胜者,只有战败者。 这里照顾的是一些年龄最大的人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权签署一份向他们表明“不抢救”的文件。他们将不会得到抢救,因为数据表明,在此次疫情范围内,超过70岁的人不会靠插管活下来。 我加入了团队,但没有人因此停止工作。没有时间。我骑上了一匹飞奔的马。我开始查看病人的病历。在去看他们之前,我要学习穿衣、脱衣、洗手,容不得丝毫错误的程序。然而,没有足够的物资用于遵守…… 在我动身前往科室时,走廊里传来难以安慰的呼喊声,并且在不断哀求。这是一个无法忍受临终时刻远离亲人的病人。有太多相爱的人不知道他们刚刚度过了在一起的最后时刻。新冠病毒是白刃,它悄无声息地置人于死地,留下一片血海。 [16:00]我没带午饭。医院的食堂和就餐室都关闭了,只有远处的咖啡店营业。幸运的是在住院实习医生办公室有巧克力。我边吃边工作,看一位病人的临床病史。午后剩余时间也都是在工作。 维克托周四接待的那位85岁的爷爷,据医生们估计,有可能在当天夜里去世,可他现在还活着。今天,他已经成了我的病人之一。他将不会留下来太久。这一次,他可能将在夜里离开。多亏了治疗,他感受不到身体疼痛。相反,他在精神方面极为痛苦,因为他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女儿,死亡决定将他带走,而他们却无法再见。他可能想要反抗,想要搏斗,并且想要对抗这令人厌恶的命运,可他没有精力,依然束手无策。甚至哭泣于他都是不可能的。他只能用难以落下的一层泪水蒙住双眼。 [20:00]维克托来找我,对于今天来说,这就足够了。他将我载回家。自行车今天晚上将留在医院。没有力气蹬车了。我该休息了,因为我们此刻还在为战斗做准备,我们还没有到它最严酷的时候,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更糟。 今晚,我把自行车放在了医院。在回家的时候,对两个人平静在一起的渴望十分强烈。我没有勇气在巴黎的寒冷中骑车了。维克托是我的男朋友,也在医院工作。我对他笑,然后问他:“如果我和你一起回家,麻烦你吗?”维克托大笑。“显然不,小可爱!”我们一起离开了这个白天是我们舞台的满是病菌的世界。 晚上,就像维克托一样,我尝试重新成为一个正常人,忘记战争。我们需要恢复过来,做好准备去迎接第二天新的战斗。 有时候,我们甚至嘲笑我们的敌人。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:我们知道可能有一天它会向我们袭来,侵略我们,给我们带来大量痛苦。真糟糕。人类是脆弱的,有时候,空气特别沉重的时候,需要放松。 今晚,离开医院后,维克托冲我说:“来一个新冠病毒下的吻?”我们就在大街上,一边笑着,一边继续走着,隔着不规整的口罩亲吻。就是这样,有时候我们用自吹自擂来替代恐惧。因为战争并不只有眼泪、流血和死亡。尽管有着悲伤和沉重,这可能也是爱情、人性的闪光在让人们不至于沉沦。 维克托还说:“真是奇怪的一天。”新冠肺炎病房的医生们经历着一种奇怪的无力感。病人众多。那些正在康复的病人需要护理,但这并不是非要在医院进行不可。那些重症患者需要转移到ICU病房,他们也知道并不一定有床位。实际上,新冠肺炎病房主要是在护理那些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病人。 我们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个是留给年轻人的。年轻人的病症通常能得到控制。如果他们好转了,我们就将他们送回各自家中。如果他们的状态有波动,就会继续留观。如果他们出现严重呼吸困难,我们就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将其送往ICU病房。 第二个是留给年纪最大人士的。对他们而言,ICU不是选项,甚至只是梦想。老人们太脆弱了,无法承受或者难以承受,而且我们也找不到床位。因此需要在大厅里处理,尝试恢复那些可以恢复的人。当不再有希望的时候,就开始临终关怀护理从而让他们在安详中离开。很显然,在他们不得不远离亲人孤独死去的情况下,这是不可能的。也许他们没承受什么身体上的痛苦,但他们肯定在精神上十分难受。 第三个部分留给那些病情没有真正改善,但呼吸状况还没有恶化到转入ICU的人。我们更多是在呼吸科看护他们。 所有病人都入院很长时间了。因为病人的变化缓慢有时无法预测。而且,当病人80岁的父母就在家里的时候,怎么能把感染的病人送回家呢?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寻找别的解决办法,但并不总能找到。 正常情况下,当病人入院后,需要经常观察,因为状态会不断变化。需要根据身体状况和对治疗的反应而调整护理,需要保持警惕。这些都是对的。但是显然,目前的情况是不同的。我们将其余事情暂缓。我们基本不做完全的医疗成像,不去监督患者验血情况变化。以后可能会设立后续照料计划,但现在真的不是做这些的时候。根据病人流量,我们在急诊室或者在候诊室。 维克托说:“事实上,我太紧张了。”他继续说:“当没什么特别情况发生的时候,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。很显然我能松口气,但我依然不动,我感到无力。我知道我们应该以协调和有组织的方式行动。根据病人数量改变工作地点可能是无法实现的,会导致混乱。我的腿休息过多的时候,我的心跳得就更快。”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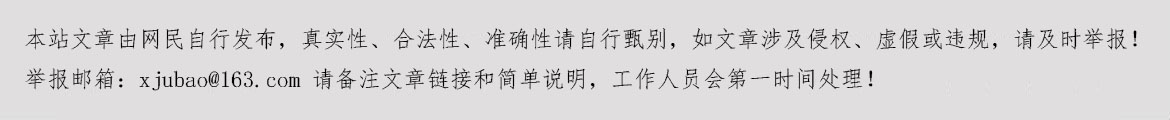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

